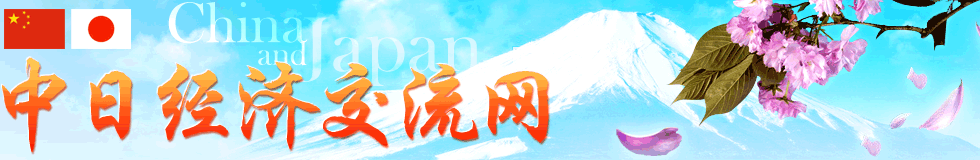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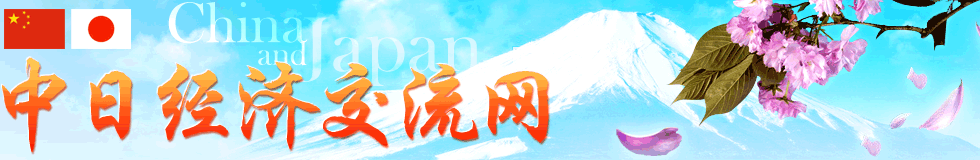

▲陳洽群(中)與日本律師緒方浩(左)商議索賠事宜。
“時效滅失”
1972年2月26日,“中威船案”第十庭在日本法院開庭。
當陳洽群向法官當庭交上自己的身份証明時,已經和被告人坐到一條板凳上的東京簡易裁判所以身份審核需要時間為由,推遲了應在當日做出的審判。
在之后的兩年裡,東京簡易裁判所以各種奇怪的理由一再推遲審判時間,直到1974年10月25日,即本案在東京涉訟第十個年頭,法庭作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萬分的審判:宣稱本案因“時效滅失”而了結,原告敗訴,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宣判結束,陳洽群差點氣暈過去,“中威”一方一片憤怒指責之聲。旁聽席上的日本新聞記者都忍不住向法官提出一系列責難性問題,被告和法官不得不狼狽退庭。
事實上,在案件庭審期間,日本政府曾提出“時效滅失”的問題,他們的理由之一是:日本國於1946年頒布的《戰時賠償特別措施法》第17條規定,“在戰爭期間遭受損失的日本公民,應在本法頒布后的兩年內,向有關當局報告以求補償,逾期者此權利喪失。”
日方說“中威”未在1948年以前向日本政府請求賠償,故求償權喪失。
“這個條文寫得非常清楚,隻對日本國民適用,怎能用在居住在香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上?”葉鳴說。他認為,日本法院不對案件基本事實進行裁決,而是以“時效滅失”為由,阻止“中威”在日本繼續對原承租人大同公司索賠訴訟,其實是想借此案,堵住中國公民通過司法途徑索賠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日民間糾紛損失的口子。
“這是別有用心的違法裁判。”他說。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在當時備受矚目的船案公判之后,東京的所有報刊電台都未作一字報道。
“審判結束后,日本法院不僅向新聞界封鎖消息,還在他們公開發行的涉外案件匯編上,將這樁舉世矚目的中日民間賠償大案抹得一干二淨。”葉鳴說。
公判后第十天,義憤填膺的陳洽群在日本律師團和東京華僑總會的支持下,迅速上訴至東京高等裁判所。東京高等裁判所的法官們,在作了許多調查並召集雙方律師就“時效問題”爭論研究多次以后,告知陳洽群“此案關系政治,須等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后方能解決。”
面對這樣的結果,作為陳家代理律師的緒方浩也隻能沉默不語。
等待——對已經為船案花費了60萬美金,年過半百,頭發都已花白的陳洽群來說,就像是一口深不見底的枯井。
等待中,中日關系正在逐漸走向緩和。
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陳洽群作為香港代表,受到日本華僑總會邀請,任歡迎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但是,陳洽群也同時收到了有關方面的消息,告訴他“不宜爭訟”、“可循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
經過了幾十年的訴訟,陳洽群已經深知這起經濟案件,摻雜了太多的歷史、政治因素,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別有用心”地使用,不但不利於索賠的結果,甚至會有政治影響。因而,陳洽群言行謹慎。
陳洽群有很多關系在台灣,又與蔣緯國私交很好,台灣每年都給他發請帖,邀請他去,十幾次邀請他一次也沒有接受過。
有一次,到日本去的飛機出了問題,停在台灣中正機場,台灣方面知道他在飛機上,請他下飛機,但是陳洽群沒有下飛機。
幾十年間,陳洽群雖然已被“中威船案”拖得精疲力盡,但他始終對自己的祖國抱有深深的愛和期待。
1985年7月26日,這個等待了一輩子的老人突發腦溢血,從此半身癱瘓,語言能力喪失過半。兩年后,纏綿病榻的陳洽群正式出具委托書,指定長子陳震、次子陳春為自己合法代理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日本國和香港地區,享有“或提起訴訟或採用任何其他法律手段”,“普遍地、全面有效地配合協助中國法律事務公司律師為船舶索償案而進行的一切有關工作”的所有權利。
1980年以前,陳春一直住在上海。從他15歲開始,便常常給在香港的父親寫信,總共寫了588封,內容幾乎都是關於“中威船案”的。
從少年時起,他和哥哥陳震就是陳洽群有意培養的訴訟接班人了。
陳洽群病重之時,這一馬拉鬆式訴訟的接力棒,正式交到了陳家第三代的手中。
 |  |
(責編:任石、張璐璐)

中日經濟交流網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