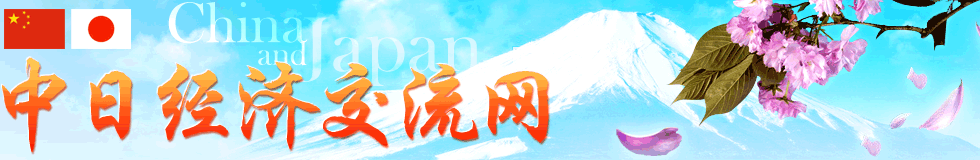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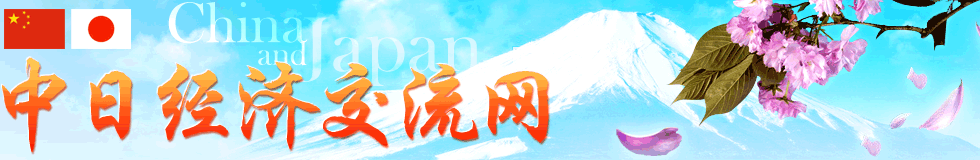

第五次開庭時的原告方。
“主體”糾紛
1987年1月1日,中國第一部《民法通則》生效實施,陳家人又有了一個新的索賠路徑。
《民法通則》規定:“凡是在《民法通則》頒布前民事權利受侵害未被處理的案件,在《民法通則》頒布后的兩年內提起訴訟都有效”。這也就意味著,已經在日本法庭被“判了死刑”的“中威船案”,終於可以在中國本土受理了。
得到這個消息,陳春立刻來到中國法律中心香港分公司,聘請任繼聖、高宗澤、司玉琢、宋楊之和江山為代理人。
任繼聖、高宗澤都曾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司玉琢曾是大連海事大學的校長,宋楊之和江山在當時也都已是知名律師。這幾位當時法律界的“大咖”,構成了后來56人律師團的基礎。
據媒體報道,時任全國律師協會會長的任繼聖先生擔任律師團團長,高宗澤先生擔任副團長。當時“中威”律師團的豪華程度,隻有文化大革命后對“四人幫”的審判能與之媲美。
后來陳家主要的出庭律師潘公波和葉鳴,就是在此時介入到案件中的。
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律系的葉鳴,在接觸“中威船案”之前,已在上海做了五年法官並獲得了律師職業資格。這個年輕的律師還在1986年中央電視台和中國法學會、《民主與法制》雜志社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法律知識競賽》電視決賽中獲得一等獎,並參加編寫出版了5本法律書籍,律師團和當事人對葉鳴很是賞識。
但在上世紀80年代末,葉鳴還不是“中威”律師團中的主要出庭律師。
1988年12月20日,“中威”正式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訴訟的對象不再是日本政府,而是大同公司的繼承者,日本海運株式會社。
“在日本審理此案時,日本政府拒絕承認扣押了‘中威’的船隻,所以在國內起訴時,‘中威’把訴訟索賠對象變成了船的原承租人——大同公司的繼承者。”葉鳴說。
1989年8月14日,上海海事法院經過對“中威船案”兩年多的審查,正式立案受理。
也就在這一年,日本海運株式會社與山下海運株式會社合並成奈維克斯海運株式會社。
1991年8月15日,上海海事法院正式開庭,一審“中威船案”。經過幾十年的累積,本案的總標的已逾1億美元。
“中威船案”第一次開庭,司玉琢和高宗澤作為原告代理律師出庭。站在主辯席上,司玉琢感受到濃濃的火藥味。
對方律師對案情的具體內容避而不談,而是提出了一個關於“訴訟主體”的質疑。
司玉琢后來曾對媒體回憶說,在第一庭的庭上,被告代理律師不斷發問,一直在“打程序”,說原告的訴訟主體中威輪船公司,早在1949年陳順通去世后就已不復存在,陳洽群、陳春先后在香港注冊的“中威”輪船公司,與老“中威”毫無關系。
第一次庭審,律師團覺得效果並不好。隨著時間的流逝,律師團中很多學者和專家因為教學任務繁重,也慢慢淡出了律師團。
“當時對陳家還有一個很不利的因素,整個90年代,上海輿論界對於‘中威船案’的報道以負面居多,一些媒體還用‘漢奸’形容陳順通租船給日本公司的行為。甚至有些法律界的人也被這個錯誤的觀念影響。”葉鳴說。
一審休庭后,1992年4月10日,74歲的陳洽群在飄搖的風雨中去世,等了一輩子,他還是沒有等到一個滿意的結果。
臨終前他向陳震以及匆忙趕來的陳春交代:“與日本的官司一定要打贏﹔跟你母親說一聲,我要先走了。”
陳洽群去世9個月后,陳春的母親也不幸去世。雙親的離去使全家陷入極度痛苦中,第二次開庭的時間也一再延遲。
“此間,因為很多法律界人士對這個案子不看好,不少人都退出了律師團。”葉鳴說,1994年底他剛剛從美國讀完法學博士學位歸國,立刻開始為“中威船案”的再次開庭做准備。
他和大學同學,同是作為原告代理人的另一位律師潘公波一起,迅速理清思路。訴訟策略轉變為以陳春、陳震為主體,追訴日本方被告違反租船合同,要求其針對損害做出賠償。
1995年1月10日,上海海事法院開始重審舊案,當時,原告的索賠金額累計已達到3億美元。
關於巨額賠償金,陳春曾明確解釋說:“我們提出這麼多的(賠償)數字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請了專門做海運海事的公司進行資產評估,我們在1995年的第四庭上派代表到法庭,出具了被告應對原告的賠償費用,測算到1995年11月30日,應該賠償312.7億日元,根據當天外匯市場的牌價,折算合3.12億美元。”
第二庭上,對方律師又就“主體資格”問題再次發難,對原告法定代表人陳洽群去世后變為陳春、陳震個人繼承及他們是否有權參加訴訟提出質疑。
“中威”一方當即反駁道:中威輪船公司是個人獨資創辦的無限責任公司。換言之,公司就是個人的商業登記,其全部權利可以通過遺囑的方式由陳氏家族的后代層層繼承。
陳順通的遺囑,給了原告方有力的証據支撐。對於主體資格的爭論,一直持續到第二次開庭即將結束時。最終,法院認為陳家兄弟合乎主體資格,其部分手續不全可予補辦,不礙庭審進行。關於“主體資格”五年的拉鋸戰才告一段落。
當年5月15日第三次開庭,原告向法庭陳述了“中威”擁有自己權利的歷史過程,當庭提交了兩份重要証據——1940年9月4日及1959年5月10日大同海運株式會社給“中威”的兩封信函。
這不僅清楚說明了“中威”一直擁有自己的權利,而且說明了“大同”對“中威”的欺騙行為。
“1940年的‘通知函’中,‘大同’對陳順通說兩艘船被日本海軍征用,實際上其中一艘(順豐)在1938年就沉沒了。這是明顯的謊言。”葉鳴說。
原告的証據如此充分,被告卻向法庭提交了陳洽群當年訴日本政府索賠材料,要求法院以此為據否定陳家現在對被告的索賠。
被告用陳洽群在日本起訴時提供的在美國存檔的資料,想証明兩船已經於1937年8月22日被日本海軍“捕獲”,以示其由於不可抗力而免責。
這是明顯的狡辯,而且,被告無法當庭提供任何支持有關其反復聲稱的兩輪被日本海軍“捕獲”應有的文件和証據。
三審又無果而終。
1996年5月20日的第四次開庭,葉鳴作為主辯律師出庭。那次的庭整整開了9天。
庭審最后,被告當庭承認對“中威”的損失負有道義責任,願意做出補貼。
從陳春第一次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至此,又過去6年,巨額賠償的前景才剛開始明朗起來。
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刻,突然又“節外生枝”地出現了另外一場爭斗——來自陳家內部的“遺囑戰爭”。
 |  |
(責編:任石、張璐璐)

中日經濟交流網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