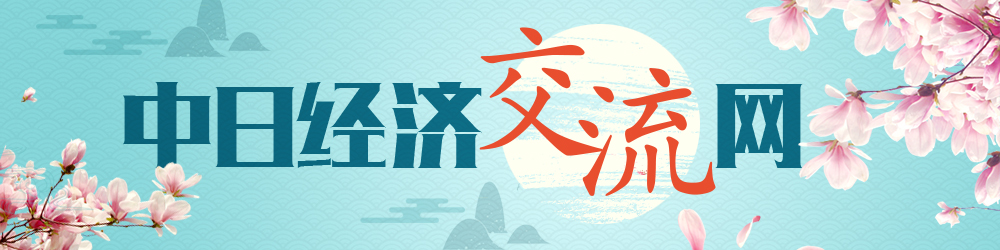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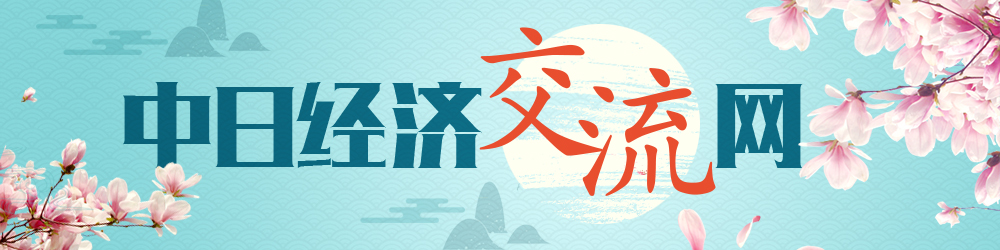
郭同慶:1987年5月,我在上海與上海外語學院留學生百子結婚。先生身體欠佳,沒能參加儀式,但他送我這個對聯,我覺得是最好的賀禮。先生的對聯是“隔海聯姻是合璧,述書有賦得傳人”。雖說我擔當不起這個重任,但是,我從那天起,就想怎樣才能不辜負先生的期待。大家都知道,搞文化搞書畫都得有一個物質基礎的保障。我后來在日本辦公司,搞進口搞承包。為了回歸書畫,把一個非常健全的公司、每年都能營利交稅的公司關掉。我作為華人能打入日本的建筑界其實是不容易的,而且能參與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館、三井住友銀行大樓、TBS電視台、富士電視台這樣的建筑。作為第二承包,就是專業承包,公司擁有從設計到加工、進口和工程管理的優秀團隊。正在那時友人拿來了日本著名金屬工匠復制的“宥座之器”。我將其放在客廳,細觀其型,試使其能。我得到莫大的啟示。回歸硯田是遲早的。因逢曾也是孔子的愛物“宥座之器”的同類器物,這促使我的回歸日程提前。回顧這回歸后的三四年,我作為專業的書法研究者投入了時間、投入了心血。面對這小小的成果,我感恩王蘧常先生厚愛和寄托。
藝術評論:關掉公司,而從事文化交流,從經濟上來說這損失其實是比較大的。
郭同慶: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和他未來的生活模式可以定一個標准,因人而異。就我個人而言,能溫飽,有院子有住宅,能不為金錢而創作,安心地搞書畫文化交流,應該是自我設計的理想的人生模式。我在上海時是一個區少年宮的窮教師。我不會過奢侈的生活。
藝術評論:您在東京的中國文化中心免費教書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郭同慶:從講座一開始的時候,2011年的10月份,到今年四年了。去年是三周年,在這與張偉生老師合作舉辦了一個中日“謙和雅集”。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與鳩山由紀夫也來的。去年的講座三周年紀念師生展的開幕式上,東京中國文化中心還特意頒發感謝狀。中國的“文化中心”開講座是作為公共的文化交流。它的定位是中國文化部駐日對外文化交流機構。這個機構一個國家隻能有一個,就跟大使館一樣。不能把它作為一個商業的基地來利用,中心主任在開講座前,跟我商量此事。為國家傳播文化,義務地開書法講座,我一口答應了。當時有很多日本人想學中國書法,大使館的官員也想學,我也有時間,我就答應下來了。一搞已三年半了。
藝術評論:講座在東京,您住在群馬,夠遠的。
 |  |